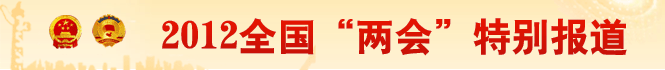3月23日,武川县特殊学校。
“同学们,今天我们上手工课。我们用包装苹果的泡沫网做小动物,好不好?”校长张美丽亲切地对学生说。“好!做个小猪!”“做个小兔子!”张美丽的一番话,让学生们兴奋起来。
20年来,张美丽情系残疾孩子,她的学生有的屡屡获奖,有的学业有成,有的当上了老板。她和学生情同母子的故事,打动了许许多多的人……
1992年,在一个临时腾出的库房里,武川县聋儿语训班开办了:一块悬挂在墙上的木板是黑板,砖上放一块木板是床,还有一个火炉、一口锅、几个碗。
“当我一进门,孩子一下扑向我,聋孩子笑呵呵地搬上板凳让我坐,智障孩子傻乎乎地拉着我的手流着口水,盲童摸着我叫老师。面对聋哑、视障和智障的5名学生,我心凉了,后悔了。”张美丽回忆。
第一节课,让张美丽终生难忘:她拿出了精心备好的教案,认认真真地给学生们讲课,却发现他们静静地坐在那里,面无表情。原来,她说的话,聋哑孩子听不到,她用手比划,视障孩子看不到。“面对这些有耳不能听、有口不能言、目光呆滞的学生们,我急得欲哭无泪。”张美丽说。
张美丽自编教材,自制教具,买回一些看图卡片,让孩子们图文对照理解内容,并让他们建立剪贴本,把看到的小动物、花、房屋等剪贴下来。张美丽通过面对面、看口型反复读和丰富的肢体语言,帮助孩子们理解并增强记忆,他们开始入门了!
1998年,武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挂牌成立,在2间不足20平方米的教室里,设有聋哑、视障和智障3种教学的复式班,共有7个年级。54名学生中有32名聋生、21名智障生和1名盲生,但只有张美丽一名教师,她既是管理者,又是任课教师、班主任,同时还是他们的生活教师、后勤人员和保育员。
特殊教育的“特”,是只能对学生实施一对一的特定教学方法,无形中一个学生就成了一个教学班。
“为了备好每个孩子的每节课,使他们有所收获,我要个个比较,人人分析,在教学的实践中研究、摸索,因人而异,因材施教。正常孩子几分钟就能掌握的知识,这些孩子得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。教30多个孩子千遍万遍地摸着喉结练习发音、说话的技巧,我的喉结红肿得像个小面包,摸一下撕心裂肺地疼,嗓子哑了就用口型。”张美丽说。
一个月、一学期、一年……孩子们渐渐掌握了发音的震动和呼吸气流的技巧,加之直观的图片,肢体语言的教学,游戏的配合,寓教于生活中,他们终于会发音了!
当年,一名4岁的聋哑孩子多次去北京求医失败,父母为他流干了眼泪,耗尽了钱财。年轻的母亲让父亲在回家的火车上把他遗弃,孩子好像意识到了这一点儿,寸步不离。无奈的父亲又把他带回了家,母亲为此离家出走。伤心的父亲就把已经6岁的孩子送进特殊学校,盼望他早日回到有声世界。
“我白天晚上一分一秒寸步不离地带着他。一年、二年、三年过去了,我在不断地摸索着各种适合他的教学方法,让他掌握发音的技巧。”张美丽说,“当他母亲在电话里听到儿子给她唱‘世上只有妈妈好’时,冒着刺骨的寒风连夜来到学校,听到儿子第一次叫‘妈妈’,她的泪水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。”
张美丽攻克了聋哑儿的语言教学,又承担起教盲文的任务。
在张美丽的努力下,盲童曹海波毕业后,办起了金梦礼仪公司,并结婚生子。
张美丽手把手地教弱智儿童怎么拿筷子、怎么穿衣、怎么上厕所等等。通过康复训练,智障孩子们可以用手机发短信了,当家长看到孩子们有如此大的变化,顿时泪如雨下。
从张美丽任教起,4岁的儿子就由姥姥姥爷带。
一次,张美丽的儿子问姥姥:“吃什么药能变成哑巴?”姥姥吃惊地看着他。“如果我变成哑巴,妈妈就会爱我,就会领着我买好多好多的好吃的!”儿子说。
“我听了母亲的叙述,望着熟睡中还带着眼泪的儿子心如刀绞。我愧疚的泪水溢满了眼眶,只能将熟睡的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……”张美丽回忆,“我儿子长大了,他上班第一个月发薪水就给每个孩子买了一个书包和文具盒,东西虽说不贵,但他却理解了我这个做母亲的心。(文/记者 张泊寒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