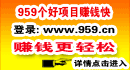聋哑少年犯突增,未管所还未来得及请专业的手语民警。笔和纸成为记者与被采访人之间唯一的沟通方式。
采访地点,设在生产车间一个角落里的办公室。
“报告”,带着白色口罩在车间打扫卫生的少年犯们时常会走进办公室。
赵东(化名),19岁,甘肃庆阳人。因盗窃罪,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。自己是聋哑人,其他少年犯不懂手语,到未教所2个月,赵东一直闷闷不乐,脾气急躁,不愿与人交流。自春节前举办了“联帮联教”活动后,赵东变化很大,时常拿笔和纸与人交流。见到记者时,他微微笑了笑。
春节前,未管所举办的“联帮联教”活动中,记者曾采访过他的母亲。据母亲赵红霞讲述,赵东是在聋哑学校上学期间,于2011年6月27日失踪,杳无音讯,直到一年后赵东被抓捕,才找到自己的孩子。因不懂手语,赵红霞至今都不知儿子在失踪的一年里,是怎么生活的。
“一个人离家出走的吗?”记者在纸上写下了问题。
一位监区民警过来提醒,要一笔一画写清楚才行,不然他不认识。
“不是,跟朋友一起。”赵东的字像小学生的笔迹,歪歪扭扭。
“朋友是做什么的?”
赵东挥挥手,不知道。
“你不信任我?”记者追问。
赵东半信半疑看着记者,片刻后他用手指了指地,伸出两根手指,又挥挥手摇摇头。看记者不懂,他警惕地左右看了看办公的民警,在纸上写道,“以前蹲过监狱,2年,是小偷,不能说”。
因家境贫寒,父亲又生病,几乎失去劳动能力,一家6口人只靠母亲一个人养活。因此赵东一直想找份工作,给家里减轻负担。一次上网时,一个称自己是聋哑人的陌生人加他QQ,并互相结识。经过20多天的联系,他们成为了“好朋友”,对方承诺要给他找工作。后来,“好朋友”来找他,并说要教他做小偷,到内蒙古“发展”,2个月给一万元“工资”。
“我不喜欢当小偷,但聋哑人找工作不容易。”一张八开纸的正反面,已被赵东写得密密麻麻。
2012年4月12日,赵东和两个“好朋友”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某停车场“闲逛”。一辆黑色轿车前座上有一个鼓鼓的钱包。第一次作案,心里慌张又害怕,“好朋友”拿出一个弹弓给赵东,并教他用石子打玻璃,他手心冒汗,心里忐忑地走到车前,“好朋友”躲在角落里,赵东左看右看,附近无人,瞄准一次,玻璃开花,不知打了几次,“砰”的一声,玻璃碎满地。
“好朋友”见成功打碎玻璃,起身跑来伸手拿起钱包就跑。跑到一个无人角落,3千多的现金,赵东第一次见那么多的钱。同样的作案,同样的手段,进行了6次。最终,被警方抓住。
母亲赵红霞说,儿子失踪有近一年时间。采访中,赵东却一直坚持,只失踪了20多天,只有2天出去做小偷,其余时间都呆在宾馆。
为何要隐瞒此事?中间又发生了什么?也许这是赵东心里一个永远不能说的秘密。
“爸爸你是不是坏人?”
采访地点换到监区办公室。经管区民警批准,3个聋哑少年犯并排坐到了沙发上,从侧面看,就像是笔直的树干。阳光透过玻璃直直地照到他们的后背。环境很温暖,很安静,但对于他们来讲,全世界都是无声的。
采访前,监区民警与聋哑少年犯在纸上沟通,“这位是记者,你们说什么都可以,心里不要有顾虑”,随后民警走了出去。
程祥(化名),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人。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。他年龄在3人中最大,有老婆,还有个8岁的儿子和8个月大的女儿。
他非常机灵,开朗。写字快,沟通起来也比较容易。
2012年初的某天早晨,他在网吧与聋哑朋友上网,出来时,见到院内一轿车里有钱包,朋友起了贪心,便砸碎玻璃偷了钱,潜逃。那时,程祥正因打麻将欠钱而苦恼,于是向该朋友借了偷来的4000元钱。
“我现在很后悔,我要好好改造,早点出去。”
春节前,程祥的老婆带着儿子,还有嗷嗷待哺的女儿来探监。程祥很开心,也很懊悔。
“儿子上二年级,是班里的组长,优秀学生。期末考试语文考了100,数学考了99。”他伸出大拇指,高兴地笑了。
“儿子问,爸爸你是不是坏人?我心里很难过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,怕影响他学习。我说爸爸不是坏人,爸爸是做了假的驾驶证才在这里,儿子说他懂。”程祥皱着眉头,满脸的忧愁。
入狱前,程祥老婆有6个月的身孕,生女儿时,他在服刑,“女儿不认识我,我出去后得多抱抱她”,未能见证女儿出生的时刻,他感到很愧疚,也很担心女儿以后不认他。
阳光温柔地挪动着脚步,三名聋哑少年犯都泛起了睡意。程祥用手搓了搓剃短的头发,提神。
程祥的老婆也是聋哑人,两人是同学。程祥被抓的地点是在家里,妻子挺着大肚子,差点吓得晕倒。程祥被带走后,他曾去找公安局局长求情。
程祥说聋哑人不好找工作,但出狱后想学厨师,每天给老婆和孩子做最好吃的饭菜。
19年的“黑人”
他,一米八的个头,皮肤白皙,粗眉,睫毛细长,坐在程祥旁边,一个劲的用手语比划着。
“19岁,无名。”程祥翻译。
他是名弃婴,收养他的爷爷奶奶也没有给起名。法院判决书的姓名栏里写的是“聋哑人”,他没有名字。爷爷告诉他,因父母嫌弃他是聋哑人,刚出生不久就送了人。好心的爷爷和奶奶收养他后,视如亲孙子。直到他15岁,两位老人同一年相继离世。从此,他便一个人生活。
没有名字,没有身份证,19年来一直是“黑人”。他有个小名叫阿贱,别人都这么叫他。收养他的爷爷奶奶家住呼市玉泉区,是农民。收养阿贱后也是百般疼爱,小时候送他去上过学,但因没钱,上完一年级就不再读书了。
爷爷奶奶不懂手语,但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与阿贱交流了15年。
家里生活贫穷,每年就靠院子里的几亩地生活。老人岁数越来越大,再无力种地,家里更加贫瘠。阿贱说,就连爷爷奶奶临走时的棺材,都是村里人出钱买的。他很感谢村里的好心人,帮他把爷爷奶奶葬在山里。
“后来去看过爷爷奶奶吗?”
阿贱用手语比划着说,他已经不记得具体位置了。
爷爷奶奶走了,阿贱又成了一个孤儿,常常到街上流浪。此间,他只要遇到用手语的人,就前去搭讪,因此也认识了许多聋哑朋友,他们都很照顾他。
他每天跟聋哑朋友在一起,有一次回爷爷奶奶的家,发现早已成废墟。没有人通知他要拆迁,没有人经过他的同意,更没有拆迁费。
家没有了,村里人也都搬走了,他只能靠那些朋友。
“我抢劫只是为了填饱肚子。”阿贱说。
2012年7月12日,阿贱在街边等候“猎物”。他恐惧,怕别人骂他是小偷。但为了生存,只能抢。形形色色的人来来往往。一名挎包推自行车的妇女,引起他注意。他跟在后面许久,趁不注意抢到包,头也不回地往前跑,但两脚就像被链子拴住一样,费劲全力,就是跑不远。不一会儿,就被辖区民警抓住,后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。
“出狱后想做什么?”
阿贱有些犹豫,“我没有身份证,找不到工作。再说吧。”
服刑改造与社会救助应同行
管区民警,要对所属管区每个犯人的家庭背景、犯罪过程等情况有详细的了解。不懂手语,民警只能在纸上与他们沟通,一次又一次,民警们也都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手语。
内蒙古未成年犯管教所四管区教导员陈宇说,服刑改造与社会救助应同时进行。聋哑人是社会中一个弱势群体,许多聋哑人因没有依靠、没有经济来源而容易受到一些不法分子的收拢。且聋哑人互相之间非常照顾,很容易成为一个社会团体,在互相拉拢中,其中任何人走入非法道路都有可能将其他人一同卷入。
陈宇说,聋哑人的内心是自卑的,他们不仅需要家人、亲人、朋友、学校的帮助,还需要更多社会的帮助和关怀。未管所每年都会开展许多活动,去积极地帮助和教育服刑人员。但服刑教育是有期限的,许多未成年犯出狱后,因得不到亲人、家庭的正确教育,或得不到社会帮助,因此而重返旧路,走入迷途。特别是聋哑人这个特殊群体,更应被社会帮助和关怀。
采访持续一天,2张八开纸,13张巴掌大的笔记本的正反面全部写满。赵东和程祥出狱后,能找到工作吗?找不到工作,最起码还有家可以回。可阿贱呢?没有名字,没有身份证,没有家,没有亲人,出狱后能到哪里?谁能收留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打工,他会不会重返旧路?
未知。(记者福荣)